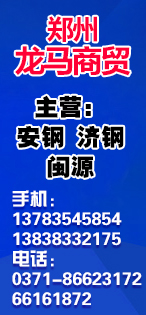从近代地价的急速攀升看中国土地的增值空间
分享打印 2002-08-22 00:00 编辑:系统管理员
来源: 字体:
[大][中][小]

由封闭到开放:地价随经济起飞飚升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然而,一个世纪前,当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国也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即由传统的封建经济,向着资本主义经济转轨,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100年间的两次经济转轨有许多相似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土地的迅速升值。首先回顾一下近代土地价格的变化。有关研究资料表明,近代中国越是新兴城市,特别是对外开放、经济活跃的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地价都呈翻番增长趋势。上海是近代经济转轨期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发祥地。以南京路为中心的上海公共租界,地处上海心脏地带,由于它开辟最早,发展最完备,所以土地价格最高,上升速度也最快。这里不仅是上海地价高峰区,也是近代中国地价最高地区。1865―1933年上海公共租界每亩平均地价增加了24.7倍,每亩平均增价率为2570%。上海市地价最昂贵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京路,南京路的地价一直处于近代中国地价史的顶峰。从1869―1933年,南京路沿路土地价格从平均每亩1616两白银增至21.4万两,上涨132倍。此前从1840年上海开埠到1869年,南京路地价已经上涨了几十倍至上百倍。以处于地价颠峰地段的沙逊大厦(今南京路与外滩丁字交口和平饭店北楼)的地基为例,1844年11月,美商琼记洋行向农民吴襄等人购入这块土地时,每亩价42两白银;1869年每亩估价6000两,上涨143倍;1877年10月31日,沙逊洋行以8万两的价格,将这块11.89亩的土地连同地上建筑买进,每亩约合6730两;1902年每亩估价3万两,1906年为10万两,1925年为17.5万两,1933年为36万两。1844―1933年的90年间增涨8570倍。广州市也不例外。1932年12月2日《中央日报》载有一段对广州市地价上升速度的调查:“以广州现时之市价而论,较于22年前(1910年),其增涨固已不止十倍,即以比之已开辟马之地,距数年之前,其价亦突涨至四、五倍,例如数年之前,普通之马路,如惠爱路、丰宁路,一德等临马路而作商店用地,每井(与每方丈面积相等)最高不过值银500元左右。较僻之马路,则值三四百元,……距今之数年间,地价突飞猛进,其增进之速度竟至出乎一般意料之外,降至现在,几有寸土寸金之势。……凡面临马路之地,放低限度,每井可值一千元,地位较优可作商店之用者,则每井地可值二三千元;繁华马路之商店地位,则非每井五千元以上不可得。”南京地价上升幅度最大的是1928年后新形成的商业区新街口、太平路、中山东路、中山北路及鼓楼一带,这些地区一跃成为市中心,地价增高数十倍以上。如新街口1922年每方丈地价仅20元,1926年为85元,1930年升至400元,1931年更达620元。10年内增值30倍。历史事实说明,在经济转轨期,增值最快的财富是土地。由低谷至高限:可观的增值空间以上仅介绍了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的最高地价,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同一城市内最高地价与最低地价的差别,就会发现一个地价增值的巨大空间。随着城市的逐步发展和完善,这个空间的经济潜能将逐步显现出来。与地价高昂的公共租界相比,上海华界地价水平偏低。整个华界面积64.7万余亩,真正的商业区和居住区只占一小部分。特别是高桥、杨思、高行三区,全是农地。所以1930年华界土地每亩平均估价只有1428元,与同期公共租界中区平均地价相比,相差105倍。天津市1860年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商业活动日趋繁忙,人口逐渐增多,近代工业出现,地价均逐年上升。但租界最低地价远远高于华界的最低低价,而华界最低地价几乎与农地相等。从各区内部的地价差别来看,1933年法租界内高低地价相差37倍,英租界内相差30倍,而华界内相差500倍。南京市各区内部1930年最高与最低地价相差35倍至158倍,全市最高与最低地价相差237倍。这些地价的差距表明,土地升值存在一个巨大空间。土地的开发利用需要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一经开始,其变化最快的就是初期阶段,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质变和飞跃。地上建筑一经完成,更新的成本将增加,变化趋向缓和。南京几个地价中心点上地价变动显示出这一普遍规律。以新街口为代表的新型商业中心地价上升速度最快,土地投机活动往往最为集中,但受政治经济动荡的打击也最为显著,波动幅度最大;以傅厚岗为代表的新型住宅区因起点地价低,土地供求关系不太紧张,地价呈稳步上升状态;以夫子庙为代表的旧城传统商业中心,因土地占用已经饱和,交易活动少,地价变化幅度最小。上述地价变动规律,在其他城市中亦有所体现。转轨期的土地价格的增值潜力,不仅显示在同一城市的不同空间上,而且表现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趋势。前面提到1844年至1933年上海南京路外滩地价增长8570倍!其增长速度已经十分惊人,但同当时世界各大城市的地价水平相比,则相差甚远。1931年正值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上海的普益地产公司曾将世界上24个大城市的最高地价进行比较,上海仅居第22位,香港第23位,广州第24位。上海最高地价与位居第一的纽约市最高地价相差33倍!这说明中国土地升值的过程才刚刚起步,后来由于诸多原因,国内这一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房地产业却进入突飞猛进的增长阶段。据日本不动产研究所调查,以1936年的地价为基数,1936年至1980年的45年间日本市街地价大约增涨9000多倍,普通农田价格也上涨1900倍之多。上述史实说明,中国的土地蕴藏着极大的升值潜力,存在着不容轻视的发展前景。因为根据城市土地价格增值的规律,地价在不同阶段的增幅不同。在城市化初期,土地由生地开发为熟地,是地价增长最迅猛的时期,但在已经过长期开发的纽约、伦敦等大城市,地价的增长已趋于平缓。可以预测,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的地价会出现惊人的增幅,土地的收益将是政府重要的财源。历史对今天的昭示:如何掌管这笔巨额财富近代中国的土地市场基本上是开放的,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在市场上公开交易。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政府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土地供给的稀缺性与私人垄断性,使土地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不能充分地解决城市土地合理配置的问题,必须借助法律、税收、城市规划等行为来实现;基础设施以及治安、防疫、消防、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是土地增值的必要条件,而这恰恰属于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范畴。政府对土地的最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莫过于基础设施建设,即供水、供电、公共交通、道路桥梁等项目。在一个地区,基础设施越完善,经济效益就越高,对人口和土地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土地集约化的程度就越高,地价增值速度就越快。在广州、厦门近代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起过重大推动作用,在天津华界新区的建设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土地专家就强调:地上设施最能影响地价者,莫过于修路。今天,西方土地经济学家仍在呼吁:政府的职责是为城市交通提供最好的条件。因交通条件改善引起地价上升的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正如当今人言“修好一条路,带动一大片”。在社会治安、消防、卫生防疫、行政管理、文化教育方面的投资与市政建设方面的直接投资相比,对土地价值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它有助于创造一种安全、文明、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氛围。人们不惜承受较高的房地产价格,来享受这一软环境效益。居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提高了那些环境优化地区的地价。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历史上也曾收效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运用了商业化的经营手段。例如通过房捐地税,将土地增值的利益转化为财政收入,作为再投资的源泉。道路桥梁实行有偿使用;公用事业如水、电、煤气、电话、市内公共交通等,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招标方式出让经营特许权、政府保持控制权的作法;大型工程通过发行公债集资,并有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杜绝浪费;连城市垃圾都由承包商售给郊区农民,1910―1920年上海有关部门仅此一项年均获利5万美元。从土地中获取财源的重要方式是征收地价税。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指出整理土地赋税是调整国家经济的关键,并提出了“照价征税,涨价归公”的原则。随着地价的上涨,要定时对土地重新估价,按新的地价标准调整税率,以便将土地涨价的利益及时收归全社会所有。1865―1933年,上海公共租界共重估地价19次,平均每三四年重估一次,也就是增税一次。1865年第一次收取地价税时,每亩土地平均估价1318两白银,1933年每亩平均估价高达33,877两白银。不到70年,每亩平均估价上涨了25.7倍。如不及时重估地价;则地价上涨的收益就会流入土地所有者个人的腰包。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同样面临如何掌管土地资产的问题。土地所有权运用得好,各级政府会从土地批租、地价升值中得到巨额回报;运用不当或一旦失控,就会成为贪污受贿的巨大黑洞,近年来滥用土地批租权力的案例屡见不鲜。我国的法律明确要求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必须实行招标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出让,集中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节省土地资源,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和制度上防止土地批租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目前全国开展土地招标拍卖活动的市县已经达到1435个。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全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款分别达到114亿元、246亿元和492亿元,今年仅有5个月就达到近300亿元。国有土地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示,成为造福于民的财富源泉。今年6月25日是中国第12个“土地日”。回看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对国土资源的前景满怀信心与期待。